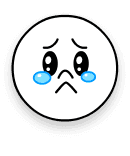自今年 7 月左右,在我所住的城市中,有件事情鬧得居民們沸沸揚揚:原因是市政府計畫要興建數座「街友導航中心」(homeless navigation center)──即俗稱的「流浪漢庇護所」(Shelter),幫助近年日益增加的街友們,能夠先有個地方安頓,再於專案人員的協助下尋找工作、重新融入社會。
然而這一個政策,卻因為「數量」與「地點」等爭議,造成當地居民們的激烈反彈──先是原先預定的 11 處庇護所,在民意的大幅反彈下一路減少到 2 處;接著由於預定地位於市中心的精華區附近,更引起許多鄰近居民的不滿。最近甚至有多達近千人,集體動員集結到市政府前抗議。
我所住的城市,位於美國加州東灣的 Fremont (費利蒙)。在美國,是亞裔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,同時它也曾拿下「加州最適合家庭居住的城市」。但若以整個矽谷、灣區來說,如今「表象」的繁華進步、房價高漲,對比背後「真實」的貧富差距日漸擴大、甚至形成「平行的兩個世界」──費利蒙頂多只是當中的一個小小個案而已。
一個「矽谷」,宛若兩個完全平行的時空
近年來,隨著南灣如帕羅奧圖(Palo Alto)、山景城(Mountain View)⋯⋯等地房價飆漲,許多科技新貴開始悄悄地移到東灣城市如 Fremont、Union City、Hayward⋯⋯等地方居住。對他們而言,在南灣僅能委身於一個小公寓的預算,在東灣可以買下一個前後有花園的大房子。加上當地環境、治安等條件均不錯,儘管通勤時間會增加,但仍是個「何樂而不為」的選擇。
然而,在同時間,這樣的「灣區內移民潮」,也將房價飆漲的狀況,從舊金山、帕羅奧圖、山景城等地擴散到整個大灣區──換言之,原本在當地就已是相對弱勢的族群,如今更難找到棲身之所了。
在這裏,「有(房)產」和「無產」者之間,更因此彷彿隔開成兩個「平行世界」:對在當地擁有房產或穩定工作的居民來說,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資產價格會不會受影響、生活環境是不是能更好;但對於另一大群不會被媒體鎂光燈照到的「矽谷邊緣人」來說,卻很可能是在自己的故鄉、卻無棲身之所的悲歌。
根據美國政府官方統計,近年來,加州一直是全美無家可歸者(homeless)人數最高的區域──更嚴重的是,當中「無安置」(unsheltered,即連基礎收容之處都沒有)的比例,更是全美最高,達 69%。而這樣的情況,還在不斷惡化當中。
加州各大城市,因此陸續投入大量預算,力求改善這個問題──然而正如文中開頭所說,廣建庇護中心的政策,一直在各地居民的強烈反對、或「NIMBY」(Not In My Back Yard 別在我家後院)的抗爭下,難以順利推行。
圖/Steve Knutson on Unsplash
想像中的美國,與真實的美國:我與舊金山街友們的「近距離接觸」
在我實際來到美國之前,總是看著許多包裝華麗、描述職場專業人士奮鬥的美劇,與個人英雄主義濃厚、「善良主角拯救世界」的好萊塢電影,一邊想像著美國人應該都是(可能有點自以為是但)富有正義感,同時勇於追求夢想,積極透過自身努力、實踐「美國夢」的一群人。
但等真的到了美國,且一開始正落腳在夢想中的矽谷重鎮舊金山之後,卻看見與想像中截然不同的景象──我看見了大量的街友在特定區域聚集、或於光鮮亮麗的大街上遊蕩,也看見「一般人」們對他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。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,赤裸裸地接觸這一切,對我來說實在衝擊很大。
這也讓我在這些年來,開始認真思考與觀察,在這個被諸如「美國夢實踐地」、「世界新創重鎮」、「獨角獸公司搖籃」等標籤所包裝的華麗舞台背後,有多少被人們忽略的社會另一面。
猶記得第一次與舊金山的流浪漢「近距離接觸」,是在當地的車站:當時我剛到美國,要去當地市政機構辦資料,在車站隔壁的超市買了一條麵包後,進站等火車。突然,身旁有一位黑人女性,指著我手中的麵包,跟我要食物──她的面容憔悴、衣著凌亂,肚子隱約突起,我不確定她是因為懷有身孕,或者是因飲食健康狀況不佳所致。
我點點頭,將手中的麵包交給她。但要到食物之後,她並沒有直接吃,而是繼續翻找著我身房的公共垃圾桶,找尋其他吃剩的食物⋯⋯。
那時,坦白說,我無法控制自己的一陣反胃:我當然知道自己應該同理對方的處境,但當下眼前的景象,與空氣中飄散的腐臭氣味,卻讓我的生理機能,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本能性地產生排斥。
此後,在舊金山的生活,我也有著許多與之相似的經驗:美國的街友們相較台灣,經常會有著更為「積極」的舉動,如主動靠到你旁邊跟你打招呼、要錢、要食物等等;或者也有更嚴重的情況,如染上酒癮或毒品的流浪漢們,在意識不清下言語威脅甚至肢體侵犯路人、偷竊或搶劫落單的觀光客等等。
在舊金山的特定街道上,更幾乎永遠充滿了大麻味、酒精味、混雜著排泄物的惡臭,與未被清理的毒品針頭。這些景象,實在與我想像中的舊金山、與我想像中的矽谷重鎮,相去甚遠。
因差異實在太大,彼此「難以同理」的現實
於是,在那段日子,我和許多長居於舊金山的「普通人」們一樣,選擇「眼不見為淨」的生活模式:
例如在通勤時,我可以選擇坐快速的公車,直接穿越 Tenderlion 區(舊金山流浪漢密集度最高、治安最不安全的地區之一)回家;或者是坐繞遠路的公車,且需要多走一大段路的方式回家──然而除非萬不得已,我必然會選擇「繞遠路」的方式。只因為,這樣可以讓我不用接觸到「另外一個世界」的景象。
那時,每當車子經過 Tenderlion 等區時,周遭無數的睡袋、難以掩滅的臭味,與許多在路邊狂笑或吶喊、疑似精神有狀況的人們,總會讓我彷彿置身在另一個自己全然不了解、也不想了解的世界中。有時候,手中拿著紙袋(裡面裝酒)的流浪漢會上車,帶著酒氣與身上的惡臭,向乘客們說話、乞討或者叫囂──他們最後往往會被司機趕下車,但緊張感仍瀰漫在空氣當中。
這些曾經有過的經驗,讓我每回下了此班公車後,總會先大呼一口氣;但緊接著還是得注意路上零星出現的流浪漢,深怕一不小心就踏到他們的「家」。
分享這些真實的經驗和心裡的真實感受,並不是要污名化所有街友們、或聳動地只聚焦社會陰暗面,而是希望點出一個事實:在貧富差距日見懸殊的大都會裡,人與人間的命運、生命經驗與生活方式,相差實在太過遙遠──這也導致了「我們」和「他們」之間漸行漸遠、甚至避之唯恐不及,直到形成真正隔開的兩個世界。
從這個角度來看一開始提到的「居民群起反對設立流浪漢收容所」的新聞,或許也就比較能夠理解:為何儘管多數人都說自己「同情街友」、「這是整個社會的責任」、「政府要好好照顧他們」;然而若將收容所設在自己家附近,就完全變成另外一回事了。
圖/ David Lundgren on Unsplash
真正的改變,先從「嘗試理解」開始
事實上,在矽谷灣區、和世界其他無數大城市中,這「貧富兩個世界」的距離,儘管都顯得越來越遙遠;如街友等弱勢族群問題,更看似是如此地無解。
然而,若要從根本改變這全球性的問題,並非無法做到的──只是政策的制定、社會福利的發放、收容所的設立等等,可能都只算是當中的「末端工程」了;真正的改變,恐怕還是要先從整體社會對「邊緣族群」的嘗試理解,開始做起。
例如,儘管在舊金山的日子,我確實因一些負面的經驗容易被放大,而對街友族群們有著本能性的迴避;但現在回想起來,其實真正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街友們,多數仍是無害、甚至除了經濟條件外,與你我並沒有太大不同的──當年走在無數往返學校與家裡、圖書館的路上,總是有一些固定會遇見的街友,他們會主動向我打招呼、或說著「妳很漂亮」之類的話。
從一開始的驚慌失措、到後來的從容應對──大方的說謝謝、並且也問候他們,我慢慢理解到,有沒有工作、有沒有住宿,並無法定義一個「人」。
我真正恐懼或排斥的,並不是「街友」族群本身,而是因他們種種在社會中的不利條件,因而衍生出比例較高的「酒精和藥物濫用」、「犯罪或侵犯他人」或「衛生不佳及疾病」等等問題──我們要對抗的,是這些社會中出現的「問題」,而不是有著這些問題的「人」。
若想要更了解美國流浪者與低薪階層的情況,我建議可以閱讀《Sidewalk》這本書:本書為一位紐約大學(NYU)的教授,親自花上 5 年,陸續深入採訪在紐約一條富人區大道上賣書的流浪漢們後,撰寫而成──從這本書中,讀者能夠更理解這群被歸類為「社會邊緣人」們不同面貌的故事、他們的想法、生活模式,以及在看似「開放、包容」的美國社會下,所隱藏的現實階級與種族差異。
另外一本書《Working Poor》,則帶出了另外一個殘酷的真相:或許,我們離「社會的另一端」,並沒有想像中的這麼遠──
作者訪問了許多在大都會中努力求生,租的房子沒有廚房、領的薪資僅只能買便宜冷凍食品,日常生活除了勞動外缺乏調劑、也缺乏奮鬥目標與升遷機會的「窮忙族」。他們當中的許多人,在這樣的日子長期下來,不只生理和心理健康都出現狀況,甚至因而開始自暴自棄,於是借酒澆愁、或因而染上毒品,走入更加難以回頭的悲慘命運。
結構性的「貧者越貧、富者越富」
誠然,「改變從理解做起」聽起來容易,但做起來難──尤其是在主流社會的想法中,始終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會認為:「失敗組」的人生,是自己造成的;或者「很多流浪漢好手好腳的,為甚麼不去工作、要沿街乞討或坐領補助?還不是自己懶散。」這樣的情況,在標榜「機會均等」、「人定勝天」的美國社會中,尤其明顯。
然而,其實不論在美國、或其他許多國家,「先天的經濟條件差異、決定了後天的命運」等結構性問題,可能才是更不可忽視的原因。舉例來說,看似標榜「機會均等」的美國,本質上仍是一個很注重信用分數、又以隱性的方法自然隔離了「窮人」與「富人」的社會:
以「信用分數」而言,一旦沒有按期繳交貸款或信用卡、信用分數降低後,要等二年以上才會再慢慢提升──在這期間,通常沒有任何正規銀行會再願意提供貸款。金融海嘯時,許多原本「正常」的中產美國家庭,就因此陷入深淵。
反觀出身富裕家庭的人,則天生擁有「高信用分數」、也更容易從金融機構借到錢,而後他們透過舉債投資房地產、股票、基金⋯⋯等,「錢滾錢」地成為更有錢的勝利組。
「隱性階級」,則是經由教育、工作、生活型態、活動地區,讓貧富兩端的世界,差距越來越大、階級也越來越難以翻轉:
例如,出身較貧窮家庭的小孩,往往只負擔得起當地的公立小學,表面上看來或許是「放任、自由、無壓力」的教育,但對於這些兩點就放學的小朋友來說,如果沒有父母或老師在一旁指引,很容易被同儕影響走入「偏門」;當然,若是在一些好區的公立小學,仍是資源非常豐富的──但前提是,父母同樣得有能力,負擔得起這些「好學區」的房價。
反觀出身中上或富裕階級家庭的小孩,從小上的是私立學校、課外活動在家庭安排下更是豐富精彩──舉凡到各地旅遊增廣見聞、到本地或外國公司實習或擔任志工、或者單純有著更多資源能夠補習、請家教進修⋯⋯。這種種因先天環境與教育方式形成的差距,往往直接決定了美國高等學府採個別申請制下的「錄取與否」;接著又因學歷差距,決定了進入產業與職場位階、收入的高低──然後同樣的模式一再複製,終成難以被跨越的鴻溝。
當然,出身微寒但靠著努力與自制,在逆境中闖出一片天,這類標準的「美國夢」故事在這裡始終都有,更經常被拿來聚焦、鼓勵著人們,然而我們也不可忽略,從比例上來說,這樣的故事,相較於美國戰後的經濟高度成長期,如今已越來越不容易見到。
最近,我時常想起李家同的《讓高牆倒下吧》這本書,裡面有一篇文章,述說著德雷莎修女從小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長,她也視自己擁有的為理所當然。直到突然有一天,她發現自己家的高牆外,原來是充滿貧窮、苦難與衝突的社會──為此她完全改變了看待世界的眼光,也促成其日後奉獻一生、為弱勢族群謀福利的志業。
在美國,如今已沒有物理上的高牆,阻隔貧富、或不同族群之間的往來。卻也和世界上許多地方一樣,仍有著一道難以突破的隱形高牆,阻絕了貧富之間的流動、與相互之間的理解。
而身在其中的我,自知沒有像德雷莎修女那樣偉大的憐憫之心;甚至在北加州住了這許多年,有時面對流浪者們仍會感到不知所措──畢竟我也只是一位來到美國,繼續努力求生、嘗試築著自己「美國夢」的平凡人而已。
但仍時時提醒自己,多些對身處「不同世界」的人們的關心與同理,並儘可能地在能力所及提供幫助──不管這「截然不同的世界」來自千里之外的國境,或是就在左鄰右舍之間。
執行編輯:張詠晴
核稿編輯:張翔一
【延伸閱讀】
●10%街友擁有高等教育文憑──他們是誰?為何流浪街頭?
●我與紐約街友席地而坐的兩小時
※本文由換日線授權報導,未經同意禁止轉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