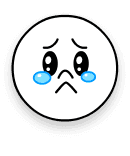每次在示威現場,見到脫下面罩休息的臉孔都會心下一緊──除下防具的他們如此年少,孩子一般的眼晴曖曖含光,臉上帶着不屬於青春的蒼涼與悲憤,社會在這個夏天給了他們難以想像的一場戰役。
世釗也一樣,下班匆匆趕到,帶着黑色的口罩,背着一個陪他出生入死的背囊,長得極瘦,加上黑衣黑褲,像襲影子,除下口罩的臉卻純真腼腆,是一張很討人喜歡的青年的臉。
6月12日,是他人生裏頭第一次聽見槍聲的日子。
6.12當日警察以催淚彈、布袋彈和橡膠子彈射向人群,有示威者和記者中槍受傷。
那下槍聲似乎打響了他的勇氣和決心,人們逃亡一般的畫面叫他畢生難以忘滅:有人頭破血流倒在地上;有人因為催淚彈而張不開眼睛,一直流淚;也有許多人在原本繁華的路上逃生驚呼,場面如同戰場;許多穿著軍裝的防暴警在後面一直揮動警棍追逐市民,他只能模仿喪屍電影的主角,不要命似的,努力保護身邊的人,並不停退後。
熟悉的城市景物這一天在他眼前土崩瓦解──天馬公園的蜻蜓、政總的小白花、中環的摩天輪和美麗的海傍迷糊了。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個小孩。
「那天過去以後,我不停參與不同的運動,叫自己習慣了那種強烈的崩潰感覺,我跟自己說,這些東西始終是要面對的,由和理非,我學習走向前線。」他說道。
夢見被人追打
然而,回家他開始發噩夢,有時夢見被人追打,一時剛夢見自己坐在家中打遊戲機,白晝見到的衝擊畫面不過是遊戲的內容。
「醒來整個人都很空虛,問自己接下來應該怎樣辦。」平日經過那些曾和警方對峙過的大街,他會顫抖冒汗,感到不安,不時「回閃」起各種被警告、追打、攻擊的畫面,連在家裏也彷彿聽見槍聲。
「有時在馬路邊,身邊有大型貨車行過,車子轟轟作響,情緒也會突然緊張起來,這些癥狀由6月到現在從未消退,有好多時候覺得自己無法承受,尤其這幾個月來食慾變得很差,常常鬧肚子,就算吞下了東西也都嘔出來,看見新聞畫面又會感覺呼吸困難,整個人變得很暴躁,很絕望,眼睛有時會突然覺得乾澀,時時都有幻覺聞到催淚彈味。」回憶時,他緊握合十的雙手,一如虔誠的教徒,然而那些畫面沒有休止般在他的腦海中重複,一直到他累極睡着為止,一旦睡去,催淚煙和防暴警又化成夢魘去折磨他。
世釗說,以前他不覺得人是那樣孤獨的,在運動的初期,他堅信前線的手足能互相保護,於是把路上穿黑衣的都視為手足,直到後來警察開始佯裝成示威者的模樣,大家開始「捉鬼」,他的信心開始瓦解。
回到家中開始害怕
他開始發現內心的恐懼叫他卑微。
「在外面可能當下是很大膽做了許多事,但回到家中就會開始害怕,不停去想一天發生的事,擔心被點相或是已被人拍下了照片。只要在街上見到閉路電視,也覺得正被人監視,連在家裏睡覺也會擔心隨時有警察上門拘捕。」世釗說,以前他不覺得人是那樣孤獨的,在運動的初期,他堅信前線的手足能互相保護,於是把路上穿黑衣的都視為手足,直到後來警察開始佯裝成示威者的模樣,大家開始「捉鬼」,他的信心開始瓦解,變成驚弓之鳥,見到有黑衣人向自己奔來,他下意識會逃走。在這一場戰爭中,大家都在心中孤軍作戰。
然而,他還是每一次的運動都參加,出門前整拾行裝變成了例行習慣,收執好就轉身離開,而每次深夜回家,他總是倒在沙發昏睡過去,直到早上才驚訝自己已經回家,梳洗完又去上班──整整三個月,每周如是過。
(AP Photo/Vincent Yu)
無畏無懼和脆弱只差一道門
「這幾個月叫我最深刻的畫面,是有次示威者來了圍我家附近的警署,我穿了整套的配備落街,但走到前面就發現已被人包抄,警察一邊講粗口一邊追我,叫我別要跑,說我沒法逃掉。於是我跑回自己的大廈,路上見到一個女生走避不及,跌倒地上,我自己幫不到她,心中很內疚。跑進屋苑後,我躲在轉角位,以為已經安全了,卻發現警察跑進來抓人,他們看見我,追着我打,最後我還是逃掉了,但回到樓上才慢慢意識到自己差一點被捕,才開始害怕,情緒崩潰。」
「另一次是在尖沙咀柏麗購物大道。防暴警那天在那裏發了好多枚催淚彈,我見到不少人中了彈,躺在地上流血,因為近距離目睹情況,加上那天食了不少催淚煙,整個人都很不對勁,覺得自己彷彿站在槍口下,被人瞄準,一邊閃避一邊要思考到底哪邊有彈,哪邊有槍,哪裏有人受傷。但有好幾下,我什麼都思考不到──在現場,我老是覺得自己是無懼的,但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的脆弱。」
「最近路經西港城,回想起一些已經遺忘的片段,記得自己曾在那裏做過許多事,面對過大大小小的恐懼,於是停下腳步,當下就出現幻覺,聽見了槍聲,忍不住一直在打顫,寒毛直豎,突然記憶起當時哪邊有防線,哪裏有警察,我即時往哪裏逃走……開始害怕,彷彿置身當時情景。」世釗很斯文,回憶起這些片段,他聲音抖顫,看來更像一個在家長日等待發落的學生,總是不安地去套弄自己的兩隻大拇指。
他說自己以前是個樂觀的人。運動開始時,不少朋友會找他談心,他默默接收別人的煩惱,到了自己再不能能承受的臨界點,只好把經歷寫上社交平台,後來甚至曾經打去關心一線。電話另一端着他別想太多,少看一些新聞,讓自己心靈好好休息,然而他打開手機,見到滿谷的壞消息,心中一沉,又變回充滿負面情緒的自己。他去看朋友介紹的催眠治療,對方用了不同方法令他放鬆,再針對不同的記憶逐一拆解。他說回憶那時的情況,總是感到不舒服,但慢慢當真正了解自己的情緒後,一切好像好轉了一點。
社會運動的陰霾不止籠罩在世釗身上,他說身邊不少前線的朋友癥狀甚至比他嚴重。
在那個沙灘上想着這一個晚霞
然而,第二天,一切又打回原形。他感到絕望。許多朋友叫他嘗試去做「港豬」,不理世事,讓自己休息。他努力嘗試,試過看新聞只看標題不看內容,但發現事態發展讓他看了標題已經憤怒。他也試過不給自己外出,但就算躲在家裏,他也無法不去看新聞,他的眼睛很難從社交平台和論壇上移開。
「我試過什麼都不帶,只是背住一個環保袋出外散步,但不知為何,走着走着就搭了車去東涌,什麼都沒有,又走上了前線。」他一邊看着眼前的幾條防線,一邊收到消息,港鐵被封了站。那就像一個士兵,雖然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卻不得不留在戰場。「而且在街上聽到別人在討論,牆上又貼了新的文宣,你就會很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,不想和社會脫節。而且曾經走過那麼前的位置,你就不會想扔下戰友,更接受不到自己留在家中做一隻港豬。」他總是上街,總是勇敢,又總是不安。臨牀心理學家後來確診他患有創傷後壓力症。
臨牀心理學家沒有像別人一樣,叫他不好看新聞,也沒有叫他不要上街,只是跟他說,他的情況處於兩難,如果不上街抑鬱情緒就會加劇,會自覺無用,但如果上街,焦慮與不安的心情又會與日俱長,創傷後壓力症難以根治。
當社會變成這樣,恐懼和動盪,避無可避,治療的病根,不是一個人,而是一個社會,需要改變的不僅是一個人的心理狀態,還不得不包括警暴問題和不人道的拘捕手法。
「這三個月,我照樣去上班,但怎樣也提不起精神,我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貢獻,無心工作,我以前好喜歡運動,但現在放棄了所有興趣,因為人活着很累,什麼都不想去做,慢慢也覺得三餐不吃也沒所謂,吃東西,只是為了填飽個肚——好幾次走進自己喜歡的餐廳,轉頭又覺得,算啦,唔食喇。」這樣折騰下來,他身體愈形瘦削,然而,他心繫的世界卻愈來愈宏大。
不知不覺,香港的夏天快要結束,他拉着夏天的尾巴,去了趟沖繩的宮古島,去看他喜歡的海。當陽光照在與那霸前濱沙灘的時候,海上片片粼光,令他不期然想起維港的晚色,海上斑斕的紫霞。